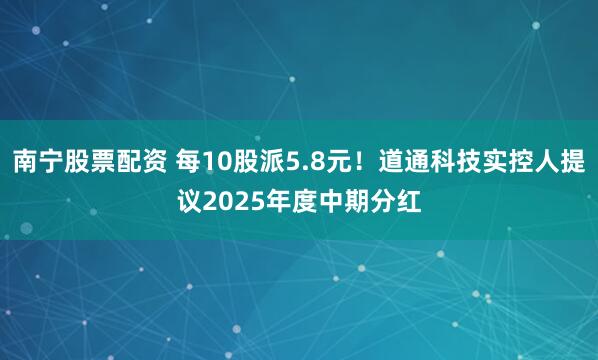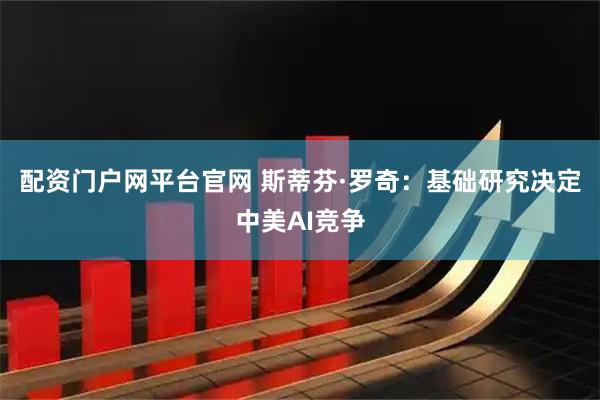
 配资门户网平台官网
配资门户网平台官网
作者:绮蝶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近期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指出,尽管从市场表现来看,美国目前在AI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但中美AI竞赛的最终赢家,很可能是能为基础研究提供更多支持、从而实现更多技术创新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在AI的长期发展中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
特朗普7月23日在华盛顿发布“美国AI行动计划”时强调,AI是21世纪决定文明未来的关键技术,美国必须“全力以赴”赢得与中国的AI竞赛。斯蒂芬·罗奇在24日的文章中称,虽然目前中美AI竞赛尚难分伯仲,但市场普遍押注美国将最终胜出。然而,先发优势并不代表最终胜利,尤其是在创新领域。如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人工智能飞跃发展的报道。美国也许凭借OpenAI的ChatGPT开创了先河,但中国的DeepSeek凭借其R1大型语言模型的成本和运算效率震惊全球。就在本月,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表现出色的Kimi K2模型,在多个关键基准测试上超越了美国的竞争对手。

▲《人工智能大模型体验报告2.0》显示,当前中国大模型产品进步显著,360智脑大模型在基础能力等方面稳居大模型第一梯队。(图源新华社)
从目前的市场现状来看,美国的确暂时领先。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近期成为全球首家市值达4万亿美元的公司(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更是全球科技界炙手可热的明星人物)。微软作为Open AI最大的投资者,紧随其后,市值达3.7万亿美元。另外,美国AI企业也在加大招揽人才。近期Meta宣布以148亿美元获得“AI数据标注独角兽企业”Scale AI半数股权,并将Scale联合创始人兼CEO汪滔(Alexandr Wang)招致麾下领导“超级智能实验室”。
斯蒂芬·罗奇认为,在高性能芯片、人才、软件和战略重点等一系列影响中美AI竞赛结果的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软件上的战略性突破,而非硬件的发展。美国无疑在半导体领域具有战略性优势。拜登执政时通过“小院高墙”政策,对先进半导体出口实施严格限制,意图遏制中国的芯片发展。然而,这一举措却适得其反,事实上刺激了中国大力自主研发AI芯片。
罗奇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在算法、模型和应用程序等软件的开发上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尽管特朗普刚刚宣布了其《AI行动计划》,但中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比其早了八年问世。衡量133个国家的创新表现、涵盖78个指标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将中国排在第11位,相比15年前的第43位实现了巨大跃升。而美国则始终稳定在第3名左右。
斯蒂芬·罗奇称,虽然《全球创新指数》(GII)框架对全球创新的起伏变化提供了全面的概览,但却遗漏了拼图中的关键一块:基础理论研究。而在这方面,政府主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指标上,美国的表现严重不佳。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官方统计,自1964年以来,联邦政府在美国研发总支出中的占比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联邦政府支出的占比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将近30%降至2023年的约10%。据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近期发布的一份详细研发评估报告,特朗普提出的2026财年预算可能会将联邦基础研究经费削减至仅300亿美元,较2025财年预计的450亿美元下降34%。按照NSF的指标计算,这将回落至2002年时的水平。

▲7月16日,来华出席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英伟达公司CEO黄仁勋表示,中国的开源AI是推动全球进步的催化剂。
相比之下,中国正在大力投入资金推进其雄心勃勃的科技创新,其2023年的研发投入占全球总额的28%,仅略低于美国的29%。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研发支出年均增幅接近14%,是美国3.7%增速的3.5倍以上,因此中美研发投入极有可能在2024年接近持平。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基于中国研发投入趋势的推算,得出惊人的结论:特朗普政府正在让美国在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领域丧失长期领先地位。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攻击”(名义上是为了废除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计划),以及日益严重的“恐华症”所滋生的反合作心态。
斯蒂芬·罗奇反问,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特朗普2.0时期的许多政策逆转,从关税到削减对外援助、再到撤回清洁能源计划。这些措施大多已被纳入保守派“2025计划”(Project 2025)蓝图之中。这份蓝图的主要目标之一原本是“倡导、参与并聚焦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如今基础研究却遭到大幅削弱,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简直接近于经济和竞争层面的“自毁”。
中国则完全相反,其一直保持对“科学发展”的重视,长期强调基础研究在中国创新体系中的支柱作用。2023年初,中国就曾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斯蒂芬·罗奇认为,当前的全球AI霸主之争常被视为两种体系的较量:市场驱动模式与国家产业政策之间的较量。但基础研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主导体系,创新最终都源于基础性的科学发现。
斯蒂芬·罗奇最后写到,如果想让创新不断涌现,就需要长期支持那些抽象、理论性强且具备广泛探索性的基础研究。作为火药和纸张的发明者,中国人早已深谙此理。不幸的是,美国或许即将通过艰难的方式再次领悟这一点。
·END· ]article_adlist-->高端访谈 ]article_adlist--> ]article_adlist-->更多访谈(下滑查看)
]article_adlist-->对话徐冰:艺术在复杂国家关系中的作用
]article_adlist-->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 -“2024香港中美论坛”高级别对话
]article_adlist-->中美关系的走向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一
]article_adlist-->影响世界现状的风险和挑战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二
]article_adlist-->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脱钩、共存、还是伙伴?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三
]article_adlist-->从气候变化到公共卫生:美中合作如何促进持久和平?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四
]article_adlist-->人文交流:信仰、艺术与文化能否为中美关系提供前进之路?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五
]article_adlist-->对话刘遵义:中国的增长之路
]article_adlist-->基金会动态
]article_adlist-->
]article_adlist-->更多访谈(下滑查看)
]article_adlist-->对话徐冰:艺术在复杂国家关系中的作用
]article_adlist-->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 -“2024香港中美论坛”高级别对话
]article_adlist-->中美关系的走向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一
]article_adlist-->影响世界现状的风险和挑战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二
]article_adlist-->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脱钩、共存、还是伙伴?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三
]article_adlist-->从气候变化到公共卫生:美中合作如何促进持久和平?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四
]article_adlist-->人文交流:信仰、艺术与文化能否为中美关系提供前进之路? -“2024香港中美论坛”分论坛五
]article_adlist-->对话刘遵义:中国的增长之路
]article_adlist-->基金会动态
]article_adlist--> ]article_adlist-->更多动态(下滑查看)
]article_adlist-->卡特总统百年纪念
]article_adlist-->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2024香港中美论坛”致辞
]article_adlist-->2024香港中美论坛“聚焦青年”
]article_adlist-->视频 | 基辛格政治遗产-2024香港中美论坛
]article_adlist-->全球遴选杰出青年 首届“CUSEF x One Young World奖学金”获奖名单揭晓
]article_adlist-->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
]article_adlist-->推荐阅读
]article_adlist-->欧洲稀土梦受制于中国
]article_adlist-->在中美之间迷失的欧盟
]article_adlist-->西方学者:中美“大交易”幻想
]article_adlist-->特朗普施政引发美国实力变化
]article_adlist-->金砖之父:G7的衰落与中美博弈
]article_adlist-->《大而美法案》透支美国增长潜力
]article_adlist-->中国对美国贸易霸权的“滴灌”策略
]article_adlist-->美国学者:赖清德近期言论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article_adlist-->从激进到灵活务实:特朗普2.0对华策略迅速升级
]article_adlist-->墙、桥还是堡垒:中美欧数据安全治理比较
]article_adlist-->旧角色与新交易:特朗普2.0时期美台关系六大变化
]article_adlist-->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
]article_adlist-->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我
]article_adlist-->觉得好看,就点个“在看”:)
]article_adlist--> ↓↓↓
]article_adlist-->【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美聚焦”】
MACD金叉信号形成,这些股涨势不错!
]article_adlist-->更多动态(下滑查看)
]article_adlist-->卡特总统百年纪念
]article_adlist-->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2024香港中美论坛”致辞
]article_adlist-->2024香港中美论坛“聚焦青年”
]article_adlist-->视频 | 基辛格政治遗产-2024香港中美论坛
]article_adlist-->全球遴选杰出青年 首届“CUSEF x One Young World奖学金”获奖名单揭晓
]article_adlist-->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
]article_adlist-->推荐阅读
]article_adlist-->欧洲稀土梦受制于中国
]article_adlist-->在中美之间迷失的欧盟
]article_adlist-->西方学者:中美“大交易”幻想
]article_adlist-->特朗普施政引发美国实力变化
]article_adlist-->金砖之父:G7的衰落与中美博弈
]article_adlist-->《大而美法案》透支美国增长潜力
]article_adlist-->中国对美国贸易霸权的“滴灌”策略
]article_adlist-->美国学者:赖清德近期言论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article_adlist-->从激进到灵活务实:特朗普2.0对华策略迅速升级
]article_adlist-->墙、桥还是堡垒:中美欧数据安全治理比较
]article_adlist-->旧角色与新交易:特朗普2.0时期美台关系六大变化
]article_adlist-->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
]article_adlist-->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我
]article_adlist-->觉得好看,就点个“在看”:)
]article_adlist--> ↓↓↓
]article_adlist-->【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美聚焦”】
MACD金叉信号形成,这些股涨势不错!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京海策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